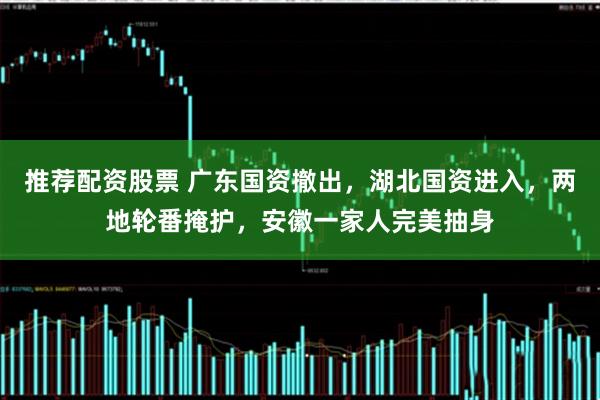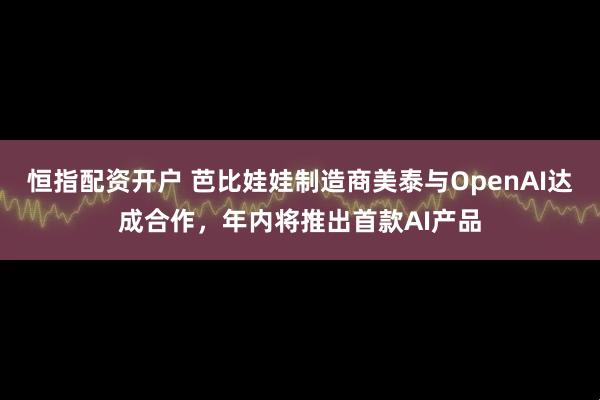王仁裕(880年—956年),字德辇,秦州长道县汉阳里(今甘肃礼县石桥乡)人。祖籍太原,祖父王义甫任成州军事判官时移居陇地。唐末五代时期大臣,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诗人。他生于大唐帝国崩塌的前夜,卒于五代乱世的末期,一生纵贯唐、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多个政权,历任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等职,目睹了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推荐配资股票,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分裂的时期之一。
王仁裕虽生于官宦之家,为人俊秀,但幼年失怙,由兄嫂抚养成人,性情孤傲,不从师训,整日“以狗马弹射为乐”。二十五岁时,才有志于学习。《旧五代史》记载,有一晚他梦见剖开自己的肠胃,去引西江水加以浣洗,又看见水中的砂石皆有篆形文字,就取来吞下。等到他醒来时,顿感心意豁朗,从此发奋苦读,工于诗文,通晓音律,禀赋极高,以文辞闻名于秦陇之地。应顺元年(934年),王思同拜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聘王仁裕为西京留守判官。后潞王(后唐废帝)李从珂反叛,王思同兵败被杀,王仁裕也被俘,但因显著的声望而幸免于难,反而被李从珂委任以翰林学士承旨(起草诏书)。当然,这和他精妙的政治智慧和处世哲学也有关系。
后世将王仁裕卓越的文才,大多归结于“感梦能文”的灵异现象,这显然是忽视了王仁裕所处的地域文化对其学识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秦汉至唐代,陇右地区已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才代出,即使在动荡与变乱交织的年代,文坛依旧星光璀璨。况且,王仁裕本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极为重视培育新人,曾主持贡举,慧眼识珠,选拔出了王溥、李昉等一大批富有才学之士,后来成为文化复兴的中坚力量,有些甚至成为执掌五代至宋初朝政的股肱之臣。可以说,在五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格局中,真正保持连续性的不是任何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以王仁裕等为代表的文化传承体系。
展开剩余76%王仁裕一生著述颇丰,有《紫泥集》《乘骆集》《周易说卦验》《入洛记》《南行记》《开元天宝遗事》《国风总类》《玉堂闲话》《王氏见闻录》等。另作诗万余首,合成百卷,因曾经梦吞西江文石的缘故,遂命名《西江集》,时人称“诗窖子”,其诗歌数量,放眼整个五代无人望其项背。遗憾的是,乱世之下王仁裕流传至今的诗文并不多,现仅《太平广记》等还辑录其二百余条佚文,《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十五首。这些诗歌文辞平实,质朴自然,体现出直抒胸臆的艺术风格。这一特点符合五代时期诗歌的整体风格趋向——逐渐摆脱唐代后期的华丽雕琢,转向更加直白真率的表达方式。由于五代时期战乱频繁,文人生活颠沛流离,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较少抽象议论和空泛抒情。
王仁裕担任秦州节度判官时曾遍游秦州名胜古迹,并现地题诗,现存较早诗作即为此时期所写的《题麦积山天堂》:
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
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
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
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身自题。
“天堂”是指麦积山巅的佛龛,现已不存。全诗真幻结合,虚实相生,以多个视角描写了麦积山峻峭巍峨的自然奇景,同时借物咏怀,既流露出年少时登高远眺、勇于攀登的豪情,也抒发了一展抱负的渴望和青史留名的壮志。
王仁裕在《玉堂闲话》中还写有一篇游麦积山的见闻: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
这详细记录了麦积山的地理位置和险峻构造,并解释了山名的由来。同时,得知一千多年前麦积山上的佛龛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应远超现今所见。因为麦积山位于地震带的交汇处,强震时有发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此地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之后历朝历代的州志里都有地震的记载。可以推断,数次地震破坏了不少佛龛。
王仁裕后文又云:
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
就此寥寥数语,包含诸多重要历史信息,引发了后世研究的三起公案。隋文帝敕赐的舍利到底葬于麦积山的何处?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的崖刻消失于何时?参与麦积山重建的到底是“七国”还是“六国”?这些至今仍无定论。所以,王仁裕的此篇游记成为研究麦积山的可贵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天福元年(936年),后晋建立,王仁裕出任谏议大夫,奉使南平国。途中见一书生因恃才傲物而全家被坑杀,悲愤之余写下《过平戎谷吊胡翙》:
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
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
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
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
以沉郁的景语起兴,以典故作结,情感层层递进,兼具哀婉与锋芒。借凭吊胡翙之死,表达了对才士蒙冤的愤慨和对那个草菅人命的世道的批判,更是深刻揭示出才华与命运、个人与时代的永恒矛盾,使得这首诗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意义。还有《从蜀后主幸秦川上梓潼山》《和蜀后主题剑门》《题孤云绝顶淮阴祠》《示诸门生》等诗,无不彰显着他痛感时事的苦楚与忧国忧民,扶危济世的情怀。
王仁裕不仅作诗,还写史。他在长安担任判官期间,遍访遗迹,采摭民言,采用笔记文体著成《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记述了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轶事、社会风俗和奇闻异事。既有唐玄宗与杨贵妃骄奢之下的长安繁华、又有李林甫、杨国忠与姚崇、张九龄等权臣博弈之间的善恶忠奸、还有“传书燕”“鹦鹉告事”“梦中有孕”具有神幻色彩的民俗传说。如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缺失的细节,也丰富了历史的表现形态。
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正担任凤翔判官的苏轼读到此书,慨然赋诗三首,现录于下:
其一
姚宋亡来事事生,一官铢重万人轻。
朔方老将风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其二
潭里舟船百倍多,广陵铜器越溪罗。
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农得宝歌。
其三
瑟琶弦急衮梁州,羯鼓声高舞臂韝。
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
三首短小精悍的绝句,如手术刀般精准剖开盛唐繁荣表象下的政治痼疾,直刺统治阶层的奢靡腐败,鞭挞权力异化与制度溃烂,暗含儒家仁政理想与历史责任感的深沉反思。这与王仁裕的治史宗旨是一致的。现今再读《开元天宝遗事》,依稀可见一个老人在驿舍的孤灯下,一边抵御窗外甲士巡夜的铁蹄声,一边用毛笔打捞一个盛世最后的倒影。
显德三年(956年),王仁裕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太子少师。“鸿笔丽藻,独步当时”的王仁裕是诗歌创作的巨匠和历史记忆的编织者,却被遗忘在诗歌长河中一段浑浊的浅滩上,眼下鲜有人知。试作一设想,倘若他的一万余首诗歌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倘若史官能给予他多一点偏爱,是否“诗窖”的名号也会如同“诗仙”“诗圣”“诗佛”一样响亮呢?(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张艳玲推荐配资股票
发布于:北京市利好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